2023太原站wtt常规挑战赛比赛时间是从11月7日开始吗?
2023-10-30
更新时间:2023-09-11 08:11:17作者:无忧百科

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】
从《奥本海默》到“两弹一星”:来自中国的“同题之作”
美国导演诺兰的历史传记巨制《奥本海默》,上周在中国内地公映。
对这个空前繁荣的暑期档,此片有资格和分量,来为之画上圆满句号,毕竟,此前它在全球已取得8亿多美元票房,中国上映5天后收益也突破2亿人民币。
何况9月初正值抗战胜利纪念日,加上日本核污水排海引发的公共话题,《奥本海默》以二战、核武器研发、广岛长崎投弹等为故事背景,多少也扣上了实时热点。

不过,观众对《奥本海默》的评价却呈现了较鲜明的两极分化:有人大赞其深邃、丰富、表演精湛,也有人吐槽沉闷、冗长、昏昏欲睡。
的确,这电影不以反转、解密、动作戏、绝地营救、大场面战争见长,它角色繁多、对白密集,极考验观众的信息抓取归纳能力,若你仅抱有“看原子弹爆炸奇观爽一把”的动机,多半鸡同鸭讲。
但它最大的观影门槛,体现在与复杂美国政治史的指涉关系上:无论是围绕在曼哈顿计划外的美苏隐性博弈,还是政府、军方、情报系统和科学界之间错综复杂的勾心斗角,抑或战后麦卡锡主义盛行、对左派的怀疑迫害,都有其自身的深层逻辑,不为普通中国观众的知识结构能迅速理解。
既然这份不习惯来自语境陌生的“水土不服”,大家会很自然把目光转回本土,转回同样拥有原子弹、且同样为原子弹付出过艰辛努力的“自己的祖国”。
何况,已有不少网友看完电影后由衷感怀:以彼时美国国力,有战争紧迫性在前、有从世界各地避难而来的一大群专家襄助、有20亿美元拨款,天时地利人和,尚且如此坎坷才把原子弹研制成功;相比之下,一穷二白、百废待举、孤立无援自力更生的新中国,能完成这项伟业,无疑更接近人间奇迹。
《奥本海默》等于在无意中,用大洋彼岸的他者镜像,为大家普及了、确证了、强化了本国前辈曾经践履的壮举,有多不可思议。
一来二去,全聚焦到一个问题:中国影视工作者,是否也演绎和诠释过,属于自己的《奥本海默》?
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
早在1991年,中央电视台摄制《中国神火》,便首次将镜头对准原子弹试验,开此一序列故事讲述的先河。
1999年上映、陈国星导演、李雪健和李幼斌主演的《横空出世》,在豆瓣拥有9.4的超高评分,不少人敬称其为“史上最牛主旋律”,至今还常常要翻出来“燃爆”一回。

2009年的《邓稼先》和2012年的《钱学森》,以二位功勋人士的真实经历及心路为基轴,条理清晰,平静而扎实,是两部比较工整的传记片。
2011年的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》,40集篇幅,是目前为止最完整、最大体量展示“两弹一星”工程的史诗正剧。
2019年的献礼剧《激情的岁月》和《那些年我们正年轻》,则开辟全新视角,主动尝试了更日常化的表达。
近年国庆档颇有影响力的、名导与明星荟萃的“我和我的”系列中,亦有两个篇章将目光投放于此,分别为《我和我的祖国》里张一白执导的《相遇》,及《我和我的父辈》里章子怡执导的《诗》。
除此以外,还有电影《绝密工程》(2019)、电视剧《有个地方叫马兰》(2019,29集)……
至于其它一些覆盖面更广、年份跨度更大的革命历史题材,也常有部分段落涉及“两弹一星周边”,如《东方》《聂荣臻》等,此处还没统计在内。
它们,共同组成了“我们的原子弹影视家谱”。
百花齐放的叙事探索:来自中国的“殊途同归”
上述“原子弹影视”,虽没有诺兰这般国际一线导演背书、没有好莱坞的全球娱乐帝国铺路,却也同样百花齐放,以独特的形态,提供了历史的“另一种版本”。
但凡做过细读细观,即会发现,它们并非像有人谈及主旋律宣传时就必要惯性批评的“脸谱化”、“说教气”,它们积极地向艺术本体靠拢,嫁接、尝试了各种影像语言、类型要素、戏剧结构和情感氛围。
《横空出世》的一文一武双雄模式,两人性格鲜明、职能与经历各异,从互不服气、屡有摩擦到惺惺相惜、肝胆相照,提供了足够有说服力与代入感的角色成长曲线。
《邓稼先》对邓稼先遭遇核弹残片强辐射后致病、饱受病痛折磨离世的描写,充满可歌可泣的悲剧美学意蕴。
《钱学森》用可观篇幅表现了钱学森在二战后遭美国政府软禁、突破重重封锁桎梏矢志归国的历程,颇具悬念感和传奇色彩,陈坤、张雨绮等当时的一线偶像担纲主演,则为之增添了更市场化、亲民化的外观。
《激情的岁月》将核试验基地中一群青年科学家的生活与情感作为切入点,探索了严肃性大主题下的青春叙事可能。
《我和我的父辈》里的《诗》,顾名思义地赋予了“理科题材”以诗性的柔韧盛放,暴雨夜两代人对峙的极致绝望、星月夜兄妹放灯的极致浪漫、结尾处父母念诗的极致绵长,温柔和感伤中升华出的坚韧力量,促动人与宇宙融为一体,都是国产电影里罕见的工巧。

即便拿它们来与《奥本海默》对标,亦有不少潜在的相似。
以《横空出世》为例:
《奥本海默》有原作小说打底、有较成熟的文字蓝本供给改编和拍摄。《横空出世》同样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作支撑,主创团队多次亲临罗布泊核基地考察,广泛采访科学家、指战员等,足迹遍及当年生产核燃料、零部件的诸多保密工厂。
《奥本海默》翔实细致、现场感好、还原度高。《横空出世》同样用了整整60吨钢材,一比一复现了发射塔、修建了战壕工事,据说,由于片场太过真实,甚至一度让外国以为咱要重启核试验,上空的监测卫星都增加到十几颗。
《奥本海默》以政治交锋为主体。《横空出世》也没完全回避特定年代里可能发生过的误会:陆光达接受过家庭和出身的审查,甚至一度被认有“通敌”之嫌,冯石将军则远赴北京,以脑袋为搭档担保,保证了研究攻关的继续进行——这份肝胆相照的磊落,倒是与《奥本海默》中施特劳斯等政客对科学家的频繁掣肘,形成了云泥之别。
《奥本海默》最被肯定和嘉许的哲学意蕴——属于人的纠结、矛盾与内在挣扎,我们的作品也不是没有触及过。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中的《相遇》里,为了保守自己所参与的原子弹这一国家机密,张译饰演的研究员主动切断了与女友的关系,失踪整整三年。电影无怨无悔地歌颂着奉献,却又始终在这三年的痛楚中闪回复述。最后一幕高潮是群众游行的段落,欢呼的人潮涌来,将研究员和女友吞没、隔开、越冲越远、直到彻底分离。
这固然是国家的荣誉、人民的意志、历史境遇的重任和嘱托,但这也是两个人被从此更改的一生、是命运的捉弄、是没有墓碑的爱情无疾而终,从画面到心绪,导演直面了神圣、无悔、勇毅、坦然,直面了个体承担的悲情,直面了委屈、遗憾、无奈和怅惘。
说完了“一样”,再来说说“不一样”。
也许,某种意义上,“不一样”更能显出价值,因为,讲中国故事,总该提供一些美国人讲不出的角度与内核。
集体主义和理想情怀:来自中国的“独擅胜场”
核武器研发故事,面对一个“元困境”:谁都知道,原子弹是物、是非生命体、是做不了主角的。故而,得找到“人”,将原子弹的故事,变成人的故事。但总归故事因原子弹而起、又以原子弹为目的,人也只能与原子弹相关,方能获得资格进入故事。然而,这又容易让人工具化、元件化、乏味化。
解决方案只能是,把关系变成双向度,把原子弹的故事和人的故事,整合成“人与原子弹之间的故事”:人造出了原子弹,原子弹反过头来,也检验了人、重塑了人。
由此形成一个内在系统:人和原子弹,在每个环节里一起互动和共振。
这就导出第一重区别,被选定和原子弹一起互动共振的,是一个神人、超人,还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。
《奥本海默》的处理大家都看见了,周而复始地拆解一个人,用力极深地扎进和透视一个人。
但我们本土的那些,却广泛地、普遍地,散射到了许许多多人。
这与其说是编剧上的考虑,不如说,是社会主义、集体主义决定的方向。正如邓稼先所说:中国的原子弹绝不是哪一个人能造出来的,绝对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。
如果奥本海默是在亲历了美国政坛、舆论、媒体的造神之后,再接受了灭神的反噬,那千千万万将青春与热血洒在西北戈壁上的中国老一代科技工作者,从告别家人到埋骨罗布泊,大约在踏上征途的那一刻,就主动隐没了姓名、暗淡了荣辱、放弃了一切“被封神”的资格与欲望。

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,第一时间赶赴爆心的防化兵(资料图/共产党员网)
他们更容易被荒疏和忽略,也就更迫切地应当被记录和言说。
很自然,将目光投向戮力同心、众志成城的广大无名英雄,绘制出一代人无计得失祸福的精神图层,这件事,功德无量。
这才让那些影视剧作里,固然有毛主席周总理聂帅的高瞻远瞩,有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的超群智慧,但更多的着墨,都在基层科研人员、基地建设者、工程兵部队、工人、无条件提供支持的当地群众们身上。
这些人或者不及奥本海默那样传奇,但他们筚路蓝缕的贴地前行,自有一种无招胜有招的震撼,效果就是,当他们来到镜头画面的中心位置,哪怕仅仅对真实细节做白描式还原,就能让激动人心的力量破屏而溢:
没有计算器和电脑,用算盘珠子推演高精公式;
没有机械化运输,用手提肩扛在沙漠中搬运设备;
生活条件恶劣,有人以树皮为食,有人徒步百里寻找湖泊,风餐露宿、喝盐碱水、蚊虫叮咬、误食毒野菜……

散射有横向的(人民群众),也有纵向的(下一代):
《有个地方叫马兰》主线围绕工程兵家属,用“在核试验基地长大的孩子们”之回忆回访视角,铺叙了当年生活、玩耍、闯祸、犯错、学习的种种,他们既体验着同龄孩子难以想象的寂寞艰辛,又得以在最近距离亲历奇迹、与一段伟大事业共同成长,用整个少年时光去渐渐读懂和理解自己父辈的执着与忘我。
《我和我的父辈》里的《诗》也从父子关系展开:父亲像个传说或符咒悬浮于半空,带着深居简出、讳莫如深的背影,儿子很久都没明白你到底是干啥的,却又不知不觉地,复制黏贴了你的轨迹,“我爸爸和我以前的爸爸都死了”,这句哀伤的台词,却漫溢着对传承的暗示——接下了你的儿子,也接下了你的使命,所以赓续了死亡也输送了希望。
散射有跨越代际的,也有跨越性别的:
在《诗》这个似乎天然就由男性主宰的环境里,因为导演的女性身份,它突破了“父辈”原本单一的性别指向:“母亲”同样是“父辈”的一个决定支点。上一代里的男性很早就离开了,下一代里的男性默默目送和祝福着,他们更像是某种符号,而在更具体的地方,一寸寸推进着研究精度、终于奏出黄钟大吕的,也可以是女性。
第一重区别来自“一个人”还是“一群人”,第二重区别来自:“一个人因为原子弹被迫经历了什么”还是“一群人为了原子弹甘于和敢于经历什么”。
《奥本海默》在具象层面揭露了美国的政治腐败和虚伪自大,揭露了罗织罪名、操弄权术、构陷迫害,在抽象层面讨论了人类怎样和自己释放的魔鬼共处。
结果就是,它很吝啬去给出一场完整的理想与成功,它是怀疑主义的。

1954年,奥本海默出席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安全听证会。(图/AP)
但我们的那些,却是百分百理想主义的,它始终和情怀、奉献、牺牲有关。我们的那些主角,几乎从没发生过奥本海默式的“灵魂拷问”——自我质疑“你赋予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,这个世界却毫无准备”,也从没为“你不能作孽之后还要让人们同情你”而混沌惶惑,他们强劲,坚定、澄澈。
怀疑主义不一定是虚无,理想主义也不一定是粉饰。
因为理想,在那些时刻,真真切切地飘扬过。
这里有文化心理结构的原因:《奥本海默》像一种希腊悲剧——电影自身也频频以“普罗米修斯”为修辞意象,充盈着西方文化里的原罪意识,和基督教思想里对“自我救赎”、“末日审判”的热衷。
中国的原子弹影视序列则更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古老神话传说:夸父逐日、女娲补天、大禹治水、精卫填海,知其不可为而为之,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这样的传说朴拙、雄浑、厚重、苍凉而骄傲,豪迈的事业也必须和人格力量形成对等,由内而外地汲取泉源,后者才决定了前者所能到达的阶位和高度,所谓“仁者无敌”,此其谓也。
但更重要的,是时代、立场、国情乃至国本所决定:价值尺度和立意不同,依据的时代背景和输送的时代情绪也不同,对原子弹本身的用途和定性,也不同。
最直白地说,我们研发原子弹,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,是应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,它从头到尾都建立在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”的前提下,建立在对和平的呼唤中,一切参与者,都对党和国家有这份信任,也就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这份笃定。
知道自己的发明只是铠甲而不是魔鬼,知道铠甲不会被用于杀戮,知道不以欺负和霸凌他人为务,因而,劲往一处使、力往一处用,不会有一段彼此拆台的听证,也不会有一个“内心都还没自洽”的功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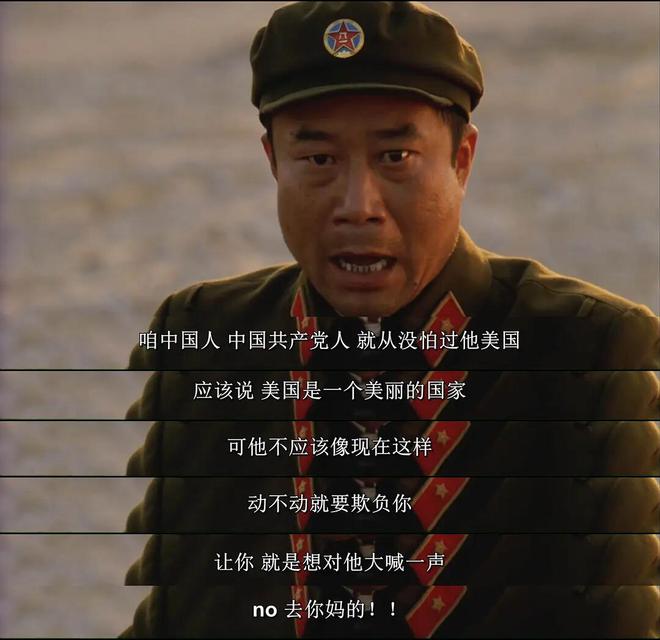
做了那么多比较,只是想要说明,《奥本海默》作为当前世界电影最受关注的作品,确有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:怎样在密集且漫长的时间线中避免流水账、加以更具匠心的取舍和裁选;怎样在内心戏和文戏里释放更多的戏剧张力……但在这个题材里,我们也不该忘记了本国的探索,和曾经的实绩。
它们和《奥本海默》间,体现的主要是“不同”,而非“优劣”,它们站位于不同的语境和诉求中,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作背景,没必要“强行拉踩”,也更无须妄自菲薄。
我们该做的,只是取长补短、继续深耕,认真思考如何在未来更好、也更自信地讲述这些,让“中国的两弹一星传奇”,具备更多对世界发声的力量与可能。
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,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,不代表平台观点,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,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,每日阅读趣味文章。
